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立一事辨析
来源:黄世喆 [大] [小] 2024-06-18
关于民盟桂林核心小组在1942年9月成立的经过,该组织的负责人梁漱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没有相关记录,其中一位成员陈此生倒是有所叙述,只是他把该组织的名称误记为“民盟西南支部”。其他成员则基本上是只字不提,甚至成员之一的千家驹不仅自认为是后来才入盟(1945年春),而且还质疑了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立一事。目前只有组织成立的关键人物之一,既是牵线人也是当事人的李伯球明确记录了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立的经过,但看上去像是孤证。因此,很值得对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立一事认真地梳理一番。
一
据李伯球等在《南方民盟斗争史略》(原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0辑)1983年12月版)中记载:
1942年7月间,李伯球应中共领导同志之邀赴重庆。8月底, 李在重庆得周恩来同志约见,向他汇报了两广情况。周恩来同志面示李伯球返回两广后要建立民盟地方组织, 开展民主运动。李伯球领命后,随即与民盟中央组织负责人章伯均商定,务求迅速在两广打开民盟的工作局面,在广西桂林请由梁漱溟、在广东韶关请由李章达主持,分别建立民盟的核心组织。
1942年9月,李伯球回到桂林后与梁漱溟会面,协商成立民盟地方组织相关事宜。就地往返多次磋商之后,他们邀请同是民盟成员的张文、曾伟、罗子为、周鲸文,成立了以梁漱溟为首的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组织成立之后,梁漱溟、李伯球又与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洽商,请他关照。不久,在桂林工作的救国会成员千家驹、狄超白等同志亦加入了核心小组。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千家驹、狄超白等同志亦加入了核心小组”的提法,这与千家驹本人的说法不一致。而我们所引用的千家驹的观点,出处是保存在民盟广西区委档案室的一封信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积极收集、整理广西民盟史料的老盟员植恒钦写给时任民盟广西区委组织部长吴天佑的,相关内容摘要如下:
最近我接到千家驹的来信,他说,救国会参加民盟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2年,这就推翻了《民盟四十周年》中《简史》所载的1942年救国会参加民盟的记录。这对我们编写广西盟史带来更多的困难了。他还说《广东文史资料》中《南方民盟斗争史略》的作者李伯球、郭翘然是第三党的,他们所说1942年9月在桂林建立民盟核心小组不确切。这是什么原因,实在很难理解。
植恒钦此信的落款是(1989年)2月4日。他不理解千家驹此番话的原因,那我们试图来释疑吧。千家驹在《自述:从昭平到黄姚》(选自中国民主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风范长存——民盟广西前辈纪念文集(1942-1949)》2011年版)当中写道:
我是在黄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时间大概在1945年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把“政团”两字取消,以便于吸收个人参加。梁漱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民盟的秘书长。桂林疏散后,梁漱溟住在八步,有一次来到黄姚,他介绍欧阳予倩、张锡昌、徐寅初、周匡人和我同时入盟。我们都填了入盟志愿书,签名盖章,志愿书写好当场焚毁。这个办法我觉得很好,既履行了正式入盟手续,又不露痕迹。
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性质,梁漱溟曾有这样的解释:凡加入同盟的党派的领导人都有双重党籍,同盟的组织纪律对加盟的独立政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因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依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联盟。(参见《梁漱溟: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选编自重庆市政协编《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联盟,既可以有双重党籍,又不一定要履行正式的入盟手续。不妨推断,当初梁漱溟牵头成立的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由于是地方组织,很可能没有举行正式的入盟仪式。而随着救国会整体加入民盟,陆续参加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救国会成员,估计也没有履行正式的入盟手续,而只是参加民盟组织活动。甚至有可能,千家驹虽然作为救国会成员参加了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活动,但是他认为只是参加民盟领导人梁漱溟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
进一步推断,千家驹之所以认为救国会参加民盟是在1945年,可能是他把民盟1944年改组后,大批救国会成员重新以个人身份加入民盟并履行正式入盟手续混为一谈了。而他就是在1945年春如此加入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的。因此,千家驹才会认为1942年9月在桂林建立民盟核心小组不确切。但无论如何,他关于“救国会参加民盟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2年”的说法是错的,由此导致了他对当年以救国会成员参加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活动也予以否认,从而质疑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立于1942年9月的事实。
二
尽管千家驹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立一事,但实际上吴天佑、植恒钦对核心小组成立一事并不困惑。
一方面,主要当事人的回忆更有说服力。除了李伯球的盟史文章,成员之一的陈此生也有关于入盟的记载:此时,救国会已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陈此生、金仲华等救国会成员加入了梁漱溟领导的民盟西南支部(笔者注:应为民盟桂林核心小组)(参见陈此生《我的自传》,中国民主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风范长存——民盟广西前辈纪念文集(1942-1949)》2011年版);而且,梁漱溟曾经在回忆陈劭先的短文中写道:“陈公劭先是我故交,……言其端要,则彼此结交盖始于一九四二年。……公暨吾乡李重毅(任仁)、李任潮(济深)诸公固皆追随孙先生革命多年之忠实党员,不甘同流合污于蒋,此时萃聚桂林。不佞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之一员。现时虽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发展盟员,其志固在团结各方以反对独裁之蒋。吾与诸公政治立场是一致的,经常在八桂厅聚晤,共商国事,此情此景,尤仿佛目前。”(参见梁漱溟《陈劭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敬志我怀念故交之感》,《陈劭先纪念文集》(广西文史资料选辑)1986年9月版)也就是说,梁漱溟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成立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但他当时是代表民盟负责(在桂林)发展盟员,既发展了盟员,相应地也应该成立组织来开展活动。
另一方面,为了写抗战时期桂林民盟的历史,植恒钦和吴天佑曾于1986年前往北京,并在民盟中央办公厅的安排下,拜访了梁漱溟,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植恒钦在《梁漱溟与中国民主同盟》(选自中国民主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风范长存——民盟广西前辈纪念文集(1942-1949)》2011年版)中记录了梁漱溟谈到有关回桂开展民盟地下活动、成立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相关情况:
梁先生说:他和李伯球见过面,是在漓江的船上,他们同乘一艘旧式木船,同睡在一个铺位上,商量在桂林开展民盟活动事宜。梁先生把他曾找过国民党省政府,申报在桂林成立民盟组织,要求给予合法地位,准许公开活动,省主席黄旭初一口回绝,说:“你(指梁)回广西工作表示欢迎,但要求成立党派,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允许的”等等,告诉李伯球。……李伯球和梁漱溟商定:既然不能公开,就建立秘密组织,开展地下活动。过了几天,也是在漓江的船上,邀集罗子为、曾伟、张文、周鲸文等开会,成立了以梁漱溟为首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
因此,在吴天佑、植恒钦看来,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立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其成员人数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梁漱溟是在回忆一开始成立组织的情形,因此并没有提及后来救国会成员加入的情况。于是,吴天佑在其负责收集、整理资料并执笔编写的《广西民盟组织简史(1942年—1949年)》(1991年编印)中写道:
民主政团同盟成员李伯球,于1942年9月到桂林与梁漱溟协商,约集张文、曾伟、罗子为、周鲸文等,组成以梁漱溟为首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不久,救国会成员陈此生、张锡昌、狄超白、胡仲持和金仲华等也陆续加入……
在此,吴天佑恰恰省去了“千家驹”的名字,比后来公认的12成员少了1名。而时任民盟广西区委主委吴克清在给《广西民盟组织简史(1942年—1949年)》写的“序言”在开篇第一句进一步说明:
民盟在广西最早建立的地方组织,是1942年抗战中期,在桂林建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小组,与当时在桂林的救国会成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引下,参加抗日救亡和民主宪政运动。
也就是说,吴克清认为,当时成立的桂林小组成员,不包括在桂林的救国会成员;或者,至少一开始不包括救国会成员。吴克清这样的提法,估计也是考虑到了千家驹的说法。但看似比较稳妥的提法,实际上容易给后人造成误会,即核心小组成员不包括救国会成员。
于是,在由两广民盟组织共同编写、曾理主编的《南方民盟历史》(1991年3月版)中,在提到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立时,关于参加组织的救国会成员人数就有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南方民盟历史》编辑委员会在“前言”中认为的“不包括在桂林的救国会成员”(估计是采信了吴克清主委的提法)因而没有提及;二是李伯球等对旧作《南方民盟斗争史略》并没有作相应的改动,仍然坚持千家驹、狄超白等同志亦加入了核心小组;三是吴天佑在其执笔的《广西民盟简史》中又作了改动,在参加小组的成员中只列出陈此生、张锡昌、胡仲持等3人,省略了千家驹、狄超白、金仲华。而狄超白、金仲华却恰恰是李伯球在其文章中强调的。当然,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是编委会或者责任编辑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写作背景而容纳了不同的说法。
拙作《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立始末》在参考借鉴上述三种不同说法的基础上,又综合后来的相关盟史回忆文章的观点,认为上述说法中提到的所有人(共12人)都算是核心小组成员比较稳妥。
三
既然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立的事实是确凿的,成员的相关人数是可以商榷的。那么,接下来就需要追问,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后,为什么就考虑在桂林成立民盟组织?而且,为什么是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亲自指导下成立的?
首先,桂林有着成立民盟组织的有利条件。一是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曾经二度聚集桂林,使桂林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云集桂林。其中,有后来以团体名义加入民盟的救国会领导人和成员: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陶行知、范长江、张锡昌、陈此生、杨东莼、狄超白、萨空了、千家驹、胡仲持、秦柳方、陈翰笙、高天、姜君辰、李任仁、陈劭先等。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香港沦陷。梁漱溟、李伯球、周鲸文等民盟成员及在香港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得到中共领导的广东东江纵队的抢救和护送,陆续安全抵达内地。之后,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在中共党员、救国会成员狄超白和张锡昌等的亲自参与、组织下,接应大多数同志到达了桂林。于是,包括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欧阳予倩、千家驹、夏衍、金山、胡仲持、金仲华等大批全国知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再次云集桂林,为重新掀起团结抗日、民主宪政的热潮聚集了力量。二是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利用广西桂系军阀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在桂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皖南事变”前,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桂系地方实力派、国民党民主人士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并团结了一大批来到桂林的进步民主人士。“皖南事变”后,梁漱溟、李伯球等民盟成员和何香凝、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到达桂林,他们与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以及李任仁、陈劭先等桂系实力派民主人士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桂林的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积蓄了力量。
其次,迫切需要在桂林成立民盟组织,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一是自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离,以及桂林“七九”事件发生后,广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遭受挫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后,1941年10月,中共南方局派李亚群等到桂林建立地区(包括柳州)党的统战工作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中共桂林文化工作小组,由邵荃麟、张锡昌、李亚群三人负责(后来狄超白加入),领导桂林抗战文化活动和文艺运动。但是当时在桂林开展团结民主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比较困难。特别是后来发生震惊广西的桂林“七九”事件,使广西省工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方工委特别交通员张海萍被捕牺牲,一批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学生、群众先后被捕。这使得广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陷入了低潮。二是已经成立一年多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亟需发展壮大,并成立地方组织。到了抗战中后期,能够称为著名“抗战文化城”的就推昆明和桂林。因此,民盟成立之后,具备发展地方组织良好条件的城市,也就是昆明和桂林。而中共南方局和民盟中央也是这样考虑的,于是有了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以及民盟昆明支部的相继成立。
具体而言。“1942年,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国统区的中共党员要加强同民主人士的联系。同年,周新民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以‘救国会’成员资格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随后,为贯彻执行中共的统战政策,他按照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到昆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参见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编《云南民盟史》,群言出版社2020年7月版)不久,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委罗隆基也到了昆明任教。罗隆基、周新民与潘光旦、潘大逵等酝酿成立组织。1943年5月5日,以罗隆基为主委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成立,最初成员仅有6名: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唐筱蓂、李公朴。
而在此前,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已经相继成立。
如前所述。1942年7月间,李伯球应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及民盟中央组织负责人章伯均电邀从桂林赴重庆。8月底,周恩来在重庆会见李伯球,让他返回两广后要建立民盟组织,以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随后,章伯均(解委会领导人)与李伯球商量如何在两广打开民盟的工作局面。他们商定,在广西桂林请梁漱溟主持、广东韶关请李章达(解委会成员)主持,在两地分别建立民盟组织,大力开展民主进步活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9月,李伯球带着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民盟中央的使命,回到桂林后立即与梁漱溟会面,转交民盟中央请梁漱溟出面主持广西盟务的信件,并协商成立民盟地方组织相关事宜。于是,他们邀请同是民盟成员的罗子为、周鲸文,以及张文、曾伟,成立了以民盟中央常委梁漱溟为首的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不久,中共南方局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张锡昌、狄超白也以救国会成员的身份参加进来。李伯球在桂林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就匆匆返韶关,向李章达转交民盟中央请他出面主持广东盟务的信件。经过协商,成立了以李章达为首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这样就使两广的两大战时重镇,开始有了民盟组织的活动。(参见李伯球、郭翘然、胡一声著《南方民盟斗争史略》,原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0辑)1983年12月版)
由此可知,相继成立的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以及民盟昆明支部,均应为民盟地方组织。但是,在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所编《云南民盟史》(群言出版社2020年7月版)一书中,多次提及昆明支部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或“最早成立的地方组织”。按《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在此书的“前言”部分所言,此书是《民盟历史文献》丛书之一,且由群言出版社所出,可以推知,此书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流的立场。如此一来,如果肯定了昆明支部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或“最早成立的地方组织”,那么,更早成立的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将不再被认可为民盟地方组织。虽说兹事体大,岂容轻议?但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还是有必要的。不过,笔者已在拙作《最早成立的民盟地方组织探究》一文中有相关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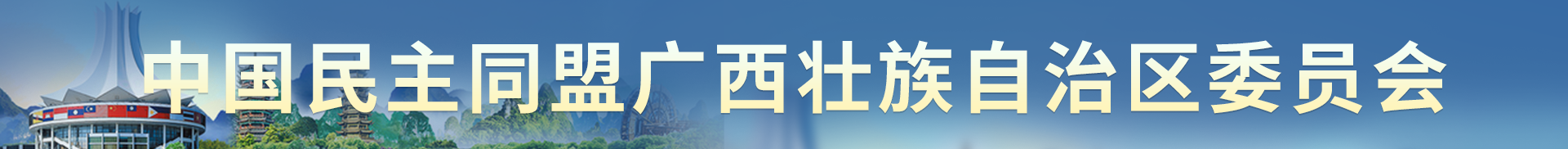

 桂ICP备08100227号-1
桂ICP备0810022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