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与东南干部会议的关系初探
来源:黄世喆 [大] [小] 2024-07-22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组织的名称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会后,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加强了对全盟组织工作的领导,在各地建立民盟地方组织,先后建立起云南省支部、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和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南总支筹委会”)、东南干部会议、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和华北总支部等地方组织。其中,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1945年春在广西贺县成立,东南干部会议1945年2月在广东梅县成立,两者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一
要谈及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与东南干部会议的关系,就要追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和韶关核心小组的成立。而这一切,又要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成立说起。
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共党组织。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就一直给予大量的支持和帮助。先是周恩来对于梁漱溟去香港办民盟机关报的计划给予支持,通过廖承志让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提供资金和人员上的具体帮助;后来又帮助民盟在桂林成立由梁漱溟牵头的桂林核心小组,在广东韶关成立由李章达负责的韶关核心小组。
这其中的大背景是,一方面民盟需要在有条件、有基础的抗战大后方城市成立地方组织;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南方局也需要在这些地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比如,1942年年底,民盟中央执行委员罗隆基到昆明筹建民盟地方组织。罗隆基到达昆明后不久,具有盟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周新民受中共组织的安排,也到达昆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在罗隆基和潘大奎、周新民等的努力下,1943年5月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支部——昆明支部。
而在此之前,两广地区已经先后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的两个“兄弟”地方组织——桂林核心小组和韶关核心小组。
两个核心小组成立之前的两广形势是十分严峻的。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桂系当局也暴露其反共本质,强令取消“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被迫离桂。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撤离后,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等到桂林建立地区(包括柳州)党的统战工作委员会,李亚群任书记,同时还建立了中共桂林文化工作小组,由邵荃麟、张锡昌、李亚群三人负责(后来狄超白成为成员),领导桂林抗战文化活动和文艺运动。
1941年12月8日,日寇入侵港九,民盟在香港的活动便告中断。香港沦陷后,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在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护送下安抵内地。原在香港从事民盟活动的梁漱溟等辗转回到桂林;李伯球、胡一声则回到惠阳见到了廖承志,商定在两广开展民盟的活动。不久,李伯球伴同柳亚子到桂林。1942年7月间,李伯球应中共领导同志之邀赴重庆。8月底,李在重庆得周恩来约见,向他汇报了两广情况。周恩来面示李返两广建立民盟组织,开展民主活动。李领命后,随即与民盟总部组织负责人章伯钧商定,务求在两广打开工作局面。
几乎与此同时,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南方局下属的派出机构)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造成当时南方工委所领导的中共江西、粤北、粤南等省委、广西省工委以及下属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没顶之灾,大批领导干部被捕,这些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几乎瘫痪。南方工委领导取消、工作暂停、下属所有党组织停止活动。两广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陷入低潮。
在此紧要关头,1942年9月,李伯球带着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和民盟总部的使命,回到桂林后立即与梁漱溟会面,转交民盟总部请梁漱溟出面主持广西盟务的信件,并协商成立民盟地方组织相关事宜。就地往返多次磋商之后,他们邀请同是民盟成员的罗子为、周鲸文,以及张文、曾伟,以秘密的形式,成立了以梁漱溟为首的桂林核心小组。不久,救国会成员陈此生、狄超白、张锡昌、千家驹、胡仲持、金仲华也陆续加入,其中狄超白、张锡昌是中共党员。救国会成员的加入,增强了桂林核心小组的进步力量;中共党员的加入,则加强了中共对桂林核心小组的指导、支持与团结、合作的力度。
李伯球在桂林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就离开桂林返回广东筹备建立民盟地方组织。他匆匆抵达广东韶关,随即与李章达协商,并转交民盟总部请李章达出面主持广东盟务的信件。李章达慨然接受了任务,于1942年10月牵头成立了以李章达为首,以李伯球、杨逸棠、郭翘然、胡一声为成员的韶关核心小组。这样就使两广的两大战时重镇,开始有了民盟组织的活动。
桂林核心小组成立后,虽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却得到了桂林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大力响应和支持,尤其是李济深、陈劭先、李任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鼎力支持和帮助。而李任仁、陈劭先也是救国会成员,他们两人负责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则成了桂林核心小组开展活动的主要阵地。同时,狄超白和张锡昌两人作为中共在桂林负责统战工作的负责人,以民盟成员和文化界人士的身份,按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此基础上,结成了包括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和有影响力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为桂林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城”,促进整个国统战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发挥了重要的特殊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陈此生除了忙于盟务活动之外,还为组织国民党内民主派的联合而奔走,经常和在桂林的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李任仁、陈劭先召开会议,以及和在广东的李章达、蔡廷锴等多次商量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韶关核心小组建立起来后,为沟通两广民盟同重庆的通讯联系,李伯球又按照在重庆时同徐冰的商定,前赴东江惠东宝游击区找寻东江游击队联系。当时东纵正为抗击国民党的重兵“围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行踪无定。李伯球历时两月,几经辗转才找到东纵,与曾生、林平、连贯等同志相会,恢复了通讯联系。
二
1944年9月,日寇从湖南入侵广西。桂林沦陷前夕,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在“八桂厅”召开有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梁漱溟、万仲文、甘介侯等6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其中,李任仁、陈劭先既是桂系元老又是广西救国会领导人,甘介侯既是桂系政客又是民盟成员,梁漱溟、陈此生则是桂林核心小组领导人及成员。会议的议题是:研究蒋介石打三次电报催李济深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事,商议对策。参加会议的人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时局的分析,即广西沦为敌后,要“大力宣传抗日保卫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李济深决定以养病为名,先回苍梧家乡,组织抗日自卫武装力量,以桂南、广东南路为活动范围,建立抗日游击区。会议决定之后,张锡昌等核心小组成员都赞成,愿意与李济深采取一致的行动,于是李济深马上行动回苍梧。
为确保滞留在桂林的民主进步人士安全,中共中央南方局两次派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赴桂林,安排文化小组的张锡昌、狄超白、邵荃麟、周匡人等人负责民主进步人士的疏散工作,主要往重庆和桂东两个地方撤退。文化小组组长邵荃麟和狄超白带一部分人去重庆;另外,为呼应李济深开辟桂东抗日新战场的行动,张锡昌、周匡人等人带领在桂林的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顺桂江而下,先后分两路向桂东转移。
于是,云集在桂林的民主进步人士包括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陈此生、欧阳予倩、莫乃群、千家驹、张铁生等被紧急疏散到贺县、昭平一带,其中梁漱溟、陈此生疏散到了贺县八步,继续在临江中学开展盟务活动。先后吸收了校长李镇、训导主任何砺锋、教务主任刘彦忠,以及教师肖敏颂、张铁生和八步日报编辑邹灌芹、文化供应社负责人之一覃展等入盟。这一时期,李济深还来到八步临江中学会见梁漱溟、陈此生等,商谈坚持敌后抗日民主斗争的问题,并邀请进步文化人士到苍梧协助他工作。
桂林沦陷后,韶关亦告急。韶关沦陷前,胡一声接到东纵的电报,要他立即到东纵去。于是离开韶关,行至淡水时巧遇杨逸棠,便一同偷越敌人封锁线,最终抵达东纵司令部,见到了林平等同志。林平对他们说:“倾得周恩来自重庆的通知,要你们协助中国民主同盟在南方建立组织,并接李章达来梅县,开展国统区的统战工作。”
胡一声和杨逸棠由东纵回到梅县后,立即与李伯球磋商,决定马上派杨逸棠和陈柏麟赴韶关接李章达,同时着手组织抗日自卫队武装。当时日寇正大举进攻华南,急于打通湘桂和粤汉两线,梅县城的国民党官员早已溜之大吉,情况十分危急。李伯球等决定立即发动群众,实行武装抗击日寇进犯,进而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李伯球在潮塘,张文(原桂林核心小组成员)、郭翘然在丙村山区,胡一声、陈炳传在梅南,陈柏麟、陈质兴在南口,分头发动当地群众组织武装。
同样在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取消同盟的团体会员制,以后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成为有党派和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在会上,桂林核心小组负责人梁漱溟(人在广西,未能出席会议)再次当选中央常务委员并兼任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核心小组成员周鲸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还是在1944年9月,中共南方局负责桂林统战工作的负责人、桂林核心小组成员狄超白赴重庆向周恩来和民盟总部汇报在桂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情况,以及李济深等准备留在粤桂敌后进行抗日反蒋的打算。周恩来指示狄超白仍回广西,继续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狄超白以救国会成员的身份再次加入民盟,并按照中共和民盟总部的指示回广西与李济深、何香凝、梁漱溟等广泛接触,发动更多的民主人士加入民盟,以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
民盟总部针对如何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的问题,也决定两广民盟组织分头行动,于1944年冬通知李章达、李伯球召开东南干部会议,筹建南方民盟组织。同时要求李伯球同东纵曾生、林平联系,并择机前往梧州与李济深、梁漱溟等共商开展南方民主抗日活动问题。
也是在1944年冬,狄超白从重庆经过昆明、百色等地,穿过敌人封锁线,几经辗转于1945年春来到昭平黄姚镇。狄超白在黄姚欧阳予倩寓所与张锡昌、千家驹、欧阳予倩、徐寅初、周匡人、莫乃群等聚会,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吸收无党派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民盟成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在桂东的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可以参加,建立组织,把工作做得更好。”接着介绍民盟总部决议关于可以吸收个人参加的内容,即文化教育界原来是民主政团同盟成员的转为民盟盟员;国民党员、中共党员都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并建立组织。随后,狄超白从昭平黄姚赶到八步临江中学,向梁漱溟传达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及转交了民盟总部指示筹建东南总支部的信件。商议完毕之后,狄超白赶赴苍梧县大坡向李济深传达周恩来的有关建议,梁漱溟、陈此生等则在临江中学成立了民盟八步支部。
不久,梁漱溟赶往昭平黄姚,主持了千家驹、张锡昌、周匡人、欧阳予倩、徐寅初的秘密入盟宣誓仪式。紧接着成立了民盟黄姚支部,徐寅初为主任,成员有欧阳予倩、张锡昌、狄超白、千家驹、胡仲持、周匡人、张铁生、莫乃群、陆联裳、朱敏、杨纳维、黄韬等。
接着,梁漱溟专程前往苍梧县大坡李济深家,请狄超白来贺县八步参加和指导东南总支筹委会的成立。梁漱溟回到贺县八步后,在临江中学召集有关人员召开会议,商议成立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筹委会委员为梁漱溟、陈此生、张锡昌、千家驹、欧阳予倩、徐寅初、周匡人、莫乃群、张铁生、肖敏颂和李镇共11人。会上,推选梁漱溟为总负责人,陈此生、徐寅初、周匡人为组织委员;欧阳予倩、张铁生、莫乃群、千家驹、肖敏颂为宣传委员;李镇为财经事务委员。梁漱溟以民盟总部代表的身份宣布东南总支筹委会正式成立,并明确了工作范围,负责推动两广、两湖、云贵、江西、福建、浙江和海外等地的民盟工作;同时,采纳了狄超白提出的工作原则,即“工作公开,组织秘密”。除筹委会组织的活动外,要求盟员结合当时各人的岗位工作,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
几乎与此同时,1945年的春节期间,李伯球等在梅县城东潮塘(李伯球的家里)召开东南干部会议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章达、李伯球、张文、胡一声、郭翘然、杨逸棠、陈柏麟、陈慰慈等十余人。会议正式宣告成立东南干部会议,并推选李章达为常设机关主任(当时会上还议定在与广西、福建取得联系后,再分别推选李任仁、何公敢为副主任),李伯球为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胡一声为宣传部长,杨逸棠为联络部长。郭翘然则以半公开身份在上层人物中开展联系工作。会上由李章达亲自草拟成立宣言。会后派李世浩、李丹出版机关报《民主》周刊。领导机关仍继续设在潮塘。
三
在东南干部会议筹备会议上,会议决定派李伯球前往东江纵队洽商后赴梧州同李济深、梁漱溟联系。但由于碰到各种困难,至8月中旬李伯球才抵达梧州苍梧李济深家,见到了民盟总部派来的先期到达的狄超白,随后又见到了梁漱溟。
由此可知,当时出席东南干部会议筹备会议的李章达、李伯球等人,在议定东南干部会议常设机关班子成员时,与在广西贺县的梁漱溟等民盟领导人长时间音讯隔绝,既不知道桂林核心小组的多数领导成员已经撤离桂林到了贺县,更不知道梁漱溟等人已经接到周恩来和民盟总部的指示,要组建东南总支筹委会。于是才会在上“议定在与广西、福建取得联系后,再分别推选李任仁、何公敢为副主任”,此举分明是要表明东南干部会议将领导广东、广西及福建的盟务工作。以至于后来广东一些地方组织的盟史文章有将“民盟东南干部会议”等同于“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甚至“亦即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部”的说法。
从现有的史料看,周恩来的建议和民盟总部的指示其实是双管齐下,先是让两广民盟组织(桂林核心小组、韶关核心小组)分别成立东南总支筹委会和东南干部会议,最终目的是在条件成熟后将二者合并、成立东南总支部。因而才有上述的李伯球抵达梧州苍梧李济深家,见到狄超白、梁漱溟之后的情形,才有“于是大家再共同协商两广民盟组织继续开展活动、成立南方民盟组织相关事宜”的表述。而且,当时若要成立南方民盟组织,不管名称是“民盟东南总支部”还是“民盟南方总支部”,组成人员(包括领导人及成员)应以东南总支筹委会为主、东南干部会议为辅。理由如下:
其一,从二者接到通知的形式看。与李伯球回到两广地区传达成立桂林核心小组和韶关小组的方式相类似,狄超白是亲自带着周恩来的建议和民盟总部的指示回到广西,指导梁漱溟等成立东南总支筹委会的。而东南干部会议则是通过东纵间接接到通知的。前面说到胡一声、杨逸棠见到东纵领导人林平时,林平说的话是:“倾得周恩来自重庆的通知,要你们协助中国民主同盟在南方建立组织,并接李章达来梅县,开展国统区的统战工作。”注意,是“要你们协助中国民主同盟在南方建立组织”。至于这“协助”二字,是协助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梁漱溟还是协助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丘哲(据广东民盟网所载,有关同盟广东省委员会简介的相关内容是:“广东民盟组织是在1942年7月至10月间,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心帮助下建立的。由盟员丘哲组建南方民盟组织,在广东战时省会韶关组成民盟韶关核心小组,以李章达为组长,李伯球、郭翘然、胡一声、杨逸棠等人参加。1945年按照民盟总部的指示,民盟韶关核心小组召开‘民盟东南干部会议’,领导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的盟务工作”),则见仁见智。
其二,从二者的名称及其领导人看。从名称上看,东南总支筹委会和东南干部会议,哪个更正式、更接近于东南总支部的筹备机构,一目了然。从领导人看,东南总支筹委会的负责人梁漱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其时再次当选中央常务委员并兼任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而李章达虽说是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当时并不在33名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之中。也许正是由于梁漱溟与李章达在民盟的身份差距比较悬殊,广东一些地方组织的盟史资料中才有了关于在东南干部会议筹备会议上“推选李济深为主任”或“选举李济深为主席”的值得推敲的说法。充其量的可能性是,当时确实有“推选李济深为主任”或“选举李济深为主席”的提议或想法,并推选了李章达为常设机关主任(另一说法为代主席)。只是由于后来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等另组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推举李济深为中央主席,李章达被选为常务理事(在李济深未到之前,李章达提议,由蔡廷锴代理主席)。“推选李济深为主任(或主席)”的设想没能实现因而作罢。但是无论如何,《南方民盟历史》编辑委员会并没有采信此说法。
其三,从二者的领导职责及工作范围看。东南总支筹委会的领导职责及工作范围,主要是负责推动两广、两湖、云贵、江西、福建、浙江和海外等地的民盟工作。这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领导职责及工作范围大致重叠。而东南干部会议则明确为领导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的盟务工作(《南方民盟历史》并没有如此明确表述)。尽管不排除两个组织由于联系中断无法互相通气的可能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东南总支筹委会的活动实际上只限于广西,东南干部会议的活动也仅限于广东,但既然两个组织均是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和民盟总部的指示成立的,因而各自所界定的领导职责及工作范围应该是有其依据的。
由此看来,“孰主孰辅”无需赘言。不过,俗话说“计划没有变化快”。如前所述,由于碰到各种困难,李伯球至1945年8月中旬才抵达梧州苍梧李济深家,见到了民盟总部派来的先期到达的狄超白,随后又见到了梁漱溟。此时由于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已经胜利、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于是需要大家再协商如何继续开展民主建国运动,以及成立南方民盟组织相关事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南总支筹委的各位成员根据各人情况,陆续离开八步、黄姚,分别赴桂林、香港、重庆等地。徐寅初、张锡昌、周匡人、欧阳予倩等到了桂林。李伯球与狄超白离开李济深家后,10月间,李伯球偕同梁漱溟、千家驹经由梧州抵广州,与李章达、郭翘然等会合。他们商定,由李伯球先到香港筹组南方总支部,便于向海内外开展活动和建立组织。11月间,狄超白、梁漱溟、千家驹、陈此生、张铁生、莫乃群、肖敏颂等也陆续抵达香港,梁漱溟短暂逗留后再转赴重庆。
由于东南总支筹委会负责人梁漱溟已返回重庆,因此,后来筹组南方总支部事宜就以东南干部会议负责人李章达为首,李伯球具体负责,东南总支筹委会成员狄超白、陈此生等亦参与其中。
1945年12月29日,民盟南方总支部在香港成立,于是东南总支筹委会就由南方总支部取代而宣告结束。李章达任主任委员,丘哲、徐傅霖为副主任委员,李伯球、张文、张铁生、陈此生、千家驹、狄超白、杨逸棠、胡一声、郭翘然等为委员。其后又补选了萨空了、胡愈之、杨伯恺、黄药眠、沈志远、郑坤廉、陈其瑗、陈汝棠为委员。稍后,莫乃群、周匡人、肖敏颂等原东南总支筹委会成员亦参加了南方总支部的领导工作。
所以,如果从周恩来和民盟总部“双管齐下”的布局看,自是不必纠缠“孰主孰辅”的问题,正如不必执着于“最早成立的民盟地方组织是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一样。由此我们初步得出如下推论:
首先,东南总支筹委会和东南干部会议是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和民盟总部的指示下建立的,目的是配合中共中央南方局共同推动南方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了中共与民盟亲密合作、共同战斗的党盟合作关系。
一方面,东南总支筹委会和东南干部会议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职责及工作范围基本一致,正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民盟总部密切配合,共同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东南地区及海外开展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有力佐证;另一方面,狄超白、李伯球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民盟总部派回两广地区的联络人,分别负责联络李济深及东江纵队,目的是开展统战工作,加强两个民盟组织与两广地区地方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系,配合李济深开展敌后抗日活动。李济深接受了狄超白带来的周恩来的建议,不仅与东南总支筹委会密切配合,还在家乡成立了“南区抗日自卫委员会”,并联系广东的张炎和蔡廷锴推动谭启秀建立“三罗”人民抗日武装,使罗定、云浮、郁南与大坡山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很好的敌后抗日政治局面。同时,周恩来多次指示东江纵队领导和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加强与东南干部会议以及李济深方面的联系。狄超白常驻李济深的苍梧老家协助其工作,李伯球则经常来往于两广民盟组织之间,联系两广地区的敌后抗日武装。
其次,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和民盟总部的指示下,东南总支筹委会和东南干部会议与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促成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诞生。
李济深本人自不必多说。东南干部会议的李章达、张文、何公敢均是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性人物,丘哲、李伯球则是早先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后来的第三党)领导人。而东南总支筹委会成员陈此生在积极开展盟务活动之余,还在李济深的领导下,与何香凝、柳亚子、陈劭先等继续酝酿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为筹备“民促”精心谋划和积极奔走,并议定了政治纲领。1945年秋,李伯球和狄超白离开李济深家返回广州时,即曾与李济深约定,一个月后到粤港会同各方共策民主建国运动。10月,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万仲文等6人在李任仁家中开会,签名发起民促,并提议李济深为会长。10月下旬,陈此生专程赴梧州拜见李济深,把拟就的民促章程和纲领交给他。李济深完全同意章程的内容并签署上自己的名字。11月,陈此生赴广州,把李济深、何香凝共同署名的章程面交蔡廷锴、李章达,请他们负责筹备成立。年底,李章达接到周恩来关于要求加速开展南方民主运动的亲笔信后,就派郭翘然到广西梧州促李济深速来广州,共商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事宜。
再次,东南总支筹委会和东南干部会议领导人及成员共同参与组建了南方总支部,他们当中大多是属于救国会、第三党成员,基本没有中间派,为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方总支部一方面坚持民盟“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方面配合中共推动南方和华侨民主运动的发展。在民盟总部宣告解散前,南方总支部就早已决定改变斗争形式,转入地下继续开展斗争。同时为保护盟员、积蓄力量,将所有有影响而又已经暴露身份的领导人和在文化界有代表性的盟员,都暂时撤到香港去,为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重新恢复民盟总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加上民盟在港组织之南方总支部、港九支部的接应,为恢复总部和接续盟务提供了便利。
1948年1月,沈钧儒、章伯钧等部分民盟总部领导人在香港告士打道 50号和成银行办事处3楼(民盟南方总支部办公地点,后成为民盟香港总部地址)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沈钧儒、章伯钧、朱蕴山、周鲸文、周新民、柳亚子、邓初民、何公敢、刘王立明、李文宜、杨子恒、李伯球、沈志远、李相符、冯素陶、罗子为、陈此生、罗涵先等出席会议,无法出席的史良、吴晗、楚图南、李章达、郭则沉、邱哲、韩兆鹗、黄艮庸、范朴斋、张云川、辛志超分别由沙千里、千家驹、周新民、萨空了、杨伯恺、云应霖、郭翘然、罗子为、周鲸文、王深林、王却尘代表(其中,李章达、邱哲、李伯球、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杨伯恺、郭翘然、陈此生、周鲸文、罗子为等是南方总支部或之前的桂林核心小组成员)。民盟南方总支部、西北总支部,上海、重庆、云南、福建支部和港九、马来亚支部的12名代表列席。南方总支部在全力支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并在批判盟内所谓“极少数人中间路线”的思想斗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民主同盟史》,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
2.《南方民盟历史》,曾理主编,《南方民盟历史》编辑委员会1991年3月印刷。
3.《云南民盟史》,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编,北京:群言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
4.《广西民盟组织简史(1942年—1949年)》,中国民主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1991年1月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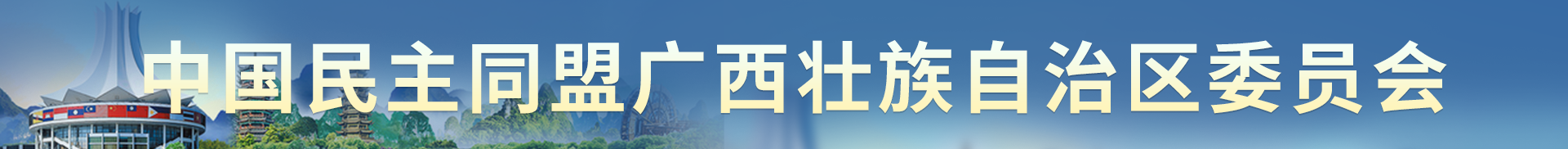

 桂ICP备08100227号-1
桂ICP备0810022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