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改组前内部各派别的情况浅析
来源:黄世喆 [大] [小] 2025-03-19
《中国民主同盟章程》在“序言”第二段写道:“中国民主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刻,由主张“团结、民主、抗日”的党派团体,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对于其中“主张‘团结、民主、抗日’的党派团体”,我们通常理解为“三党三派”,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一
我们先回顾一下民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建情况。
统一建国同志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参政会中各中间党派和部分民主人士组成的进步团体,1939年11月23日在重庆成立。参加者有“三党三派”的主要领导人,如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均、丘哲;救国会的沈均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非参政员);职教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建派的梁漱溟,以及个别无党派人士张澜、光升等人。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主张实施宪政、反对内战,各党派一律平等,拥护蒋介石为领袖等,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为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
统一建国同志会仅有几十名会员,多是国共两党以外的国民参政员,但也有不是参政员的民主人士。它为民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41年3月19日,统一建国同志会成员13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成立大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出席大会的有:职教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建派的梁漱溟;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林可玑、杨赓陶;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罗隆基(蒋匀田代);第三党的章伯均、丘哲;社会贤达张澜。
会议选举到会的黄炎培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张君劢、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同年10月,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经过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核心成员及领导机构对比,可以发现,“三党三派”的领导人当中,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成为常务委员,罗隆基(后来退出国社党)成为执行委员,罗文干、胡石青(41年2月离世)则没有当选;青年党的左舜生为常务委员兼总书记,李璜、林可玑、杨赓陶为执行委员,曾琦、余家菊没有当选;职教派的黄炎培在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初,都是主席,不久却辞去主席职务。而接任主席的张澜显得有些戏剧性:其一,他是无党派人士,非“三党三派”的领导人;其二,虽然之前在统一建国同志会被选为常务干事,但民盟成立之初只是13个执行委员之一。张澜是以执行委员身份越过其他常委接任主席职务的。至于救国会,为避免刺激国民党,在民盟成立时未正式参加,后(1942年)始由沈钧儒、张申府出面代表加入。
由于草创时期的政团同盟只是个松散的政治联盟,组织并不严密,因此在入盟及退盟方面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和严谨的程序。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其一,并非所有“三党三派”的领导人都参加了民盟的成立大会。当时只有“三党两派”参加,救国会缺席。而且,参会的13人并非所有“三党两派”的领导人。
于是我们看到,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参会的党派领导人有,青年党的曾琦、余家菊,国社党的张东荪、徐傅霖(徐梦岩),第三党的彭泽民,救国会的沈钧儒、张申府等。曾琦、余家菊直到1944年9月才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上进入领导机构,曾琦与李璜一起增选为常务委员,余家菊为执行委员;张东荪也和曾琦一样,在1944年9月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常务委员;徐傅霖则直到1946年1月,从南洋返重庆后去香港,担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副主任委员;彭泽民虽于1941 年10 月就参加民盟,但直到1947年1月才在民盟二中全会上,因民盟总部领导机构和人员的调整和充实被聘为华侨委员会主任,并于同年4月被推选为民盟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
救国会的情形有所不同。沈钧儒、张申府代表救国会加入民盟是在其成立一年之后(1942年),但民盟总部并没有因此而增选中央执行委员,所以救国会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领导人进入民盟领导机构,直到1944年9月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情况才有改观。
其二,并非所有“三党三派”的成员都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这毋庸赘言。虽然说“三党三派”的成员可以办手续成为政团同盟盟员,但是也可以不加入。而且可以说,加入的只是极少数上层人士。仅举一例,1945年10月,改组后的民盟由于可以大量吸收无党派人士,盟员人数才增长到了3000多人,其中无党派人士占70%以上,而青年党党员早就号称有10万之众;到了1947年,全国盟员总数约6000人,而青年党则号称拥有党员人数达30万之众。
甚至,有少数“三党三派”的代表性人物都没有加入民盟,比如第三党的谭平山、乡建派的晏阳初等。
其三,并非所有加入民盟的人士都是“三党三派”的成员。
虽然名为政团同盟,实际上在成立初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者亦不乏其人,如张澜、光升等“部分社会贤达”。虽然名为政团同盟,实际上各党派的领导人,主要还是以个人身份在活动,他们在政团同盟内的政治主张并不能完全代表该党派的立场。同时政团同盟内部虽然有了组织和领导,但实际上,仍是各党派首脑联席会议的性质。因此,并非民盟的所有政治主张都完全代表了所有党派的立场。
另外,关于政团同盟的性质,10月10日在《光明报》发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指出:“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接着,又在10月16日《光明报》的社论里作进一步的说明:第一,这是一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他本身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第二,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政党,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党之外,政治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第三,这一联合的前身就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社论”不否认既然民盟内部各自党派的政治立场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在原则性问题上,民盟应保持着一致性。“社论”强调民盟的成立是为了各党派的联合行动,因而其公开的政治主张就是为了体现各党派的共同心声。而这种建立在民主精神之上的一致性是通过《<光明报>言论公约》来保证的。
二
此外,有一些其他派系或者团体的成员,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了成立之初的民盟。这是以往盟史研究者易忽略的事实。
梁漱溟在《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当中,提及当年赴香港筹办《光明报》的过程时写道:
在重庆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办报时,本曾商定张君劢、罗隆基二位随后也将来港协助,但他们始终未能来。黄炎培(当时任抗战公债筹募委员会秘书长)原说去南洋募捐后途经香港时与我相会,不料我到港之日恰好他离港飞回重庆。于是有关筹办报纸的事宜,我只得会同当时在港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商讨办理,如曾慕韩(即曾琦,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即今日之农工民主党)、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筹办过程中,还与当时在港的许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接触,他们自然都对民盟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来告诉我与他联系的,因为在离重庆之前,我到曾家岩将去港办报的事告诉他,并向他问得中共驻港代表。在临创刊之时,有人又劝我出面宴请一些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记得被邀请的人士中有茅盾、夏衍、金仲华等人。
接着梁漱溟在谈及“报纸的创立与停刊”时又写道:
我去香港没有带一个人,办报的班子是到香港后才筹组的。8月接到重庆的民盟同人的信,决定由我任报社社长,经理则由我推荐萨空了(笔者注:中共、救国会,后加入民盟)担任。其余编辑人员等,多靠金仲华(笔者注:救国会,后加入民盟)等人介绍。记得新闻版领导人是笔名羊枣的(听说后来他在福州为国民党杀害)。总编辑是俞颂华(笔者注:无党派,范长江的老师,黄炎培推荐),他原在上海《申报》工作过,是个老报人。
这里所提及的一起筹备办报的相关盟员,除了通常所说的“三党三派”的领导人外,还包括别的政治团体及派别的成员。
首先是民主宪政党的领导人伍宪子(名庄)。他是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初名宪政会,后改名中国宪政党,直到1945年11月11日,伍宪子担任党主席后,才加入“民主”的元素。据其解释,中国民主宪政党之“民主”,不是与“宪政”并称,而是以“中国民主”修饰宪政,从而区别于西方民主。
众所周知的是,1946年8月,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并组成新党,取名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张君劢任主席,伍宪子任副主席。我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伍宪子此时才加入民盟。而通过梁漱溟的回忆,我们才知道伍宪子当时(1941年)已经加入民盟。又有资料显示,在民宪党与国社党合并之前的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时,该党就曾电请民盟,代为提出四项政治主张(内容略)。如此看来,由已经加入民盟的民宪党领导人伍宪子代表自己的党派向民盟提出政治主张,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其次是东北同乡会(或称东北民众自救会)的周鲸文。周鲸文于1933年《塘沽协定》后,在京津地区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杂志。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1942年9月在桂林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1944年9月当选民盟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10月在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常务委员。可见周鲸文也是民盟早期重要的领导成员之一。
再就是桂系的甘介侯。甘介侯曾于1932年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是第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甘介侯是李宗仁的亲信,李济深是李宗仁的恩人。可能正是因为他有着参政员的身份,于是奉李济深及桂系之命加入民盟。在讨论民盟纲领其中第四条“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切实执行”时,就是他坚持不能删掉的。但奇怪的是,几乎查不到他参加其他民盟活动的记载。倒是梁漱溟在广西桂林开展活动时与甘介侯有所交集,因甘介侯时常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及“宪政促进会”组织的活动。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就是“天天在搞”“改造时局”和盟务活动。“其间常常在一起,作为主要的几个人,就是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几位。”这几位除了陈此生是盟员,其他都是与桂系有关的国民党元老,后来都成了民革的创始人。而甘介侯也常常加入其中。
另据史料披露,1944年5月下旬,日军占领了长沙、沈阳,广西桂林、柳州危急。当月,李济深在桂林广西建设研究会八桂厅召开有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梁漱溟、万仲文、甘介侯等6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研究蒋介石打三次电报催李济深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事,商议对策。这个重要会议参会人数很少,甘介侯也在其中,可见其在李济深及桂系当中的地位。不过,他虽说是盟员,且在《光明报》办刊期间就与梁漱溟交往,但梁漱溟到桂林负责成立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时,并没有吸纳甘介侯加入。
当然,梁漱溟没有提及的、以及在此之后入盟的还有不少。比如后来在张澜的影响下发展的秘密盟员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张澜一直做川康两省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其醉翁之意不在小党派之间(的小团体利益),而在把地方实力派拉到抗日民主阵营之中。
另外,梁漱溟在回忆中提及的左翼人士柳亚子、彭泽民、金仲华等此时还没有加入民盟。但有资料说彭泽民于1941 年10 月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就是说,是在《光明报》创刊后不久加入的;金仲华于1943年以救国会成员的身份加入以梁漱溟为首的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柳亚子则更晚些,入盟时间是1945年7月。
而且,当时梁漱溟在香港办报,不但得到已经参加的“三党两派”领导人和成员的支持,还得到了中共、救国会以及地方实力派(如李济深、龙云、刘文辉等反蒋势力)的鼎力相助。
据梁漱溟的回忆,关于办报经费的筹措,民盟的负责人如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每人(即各派各方)出1万元。梁漱溟由于经济能力弱,出了6000元。还通过联络四川的刘文辉资助4万元,云南的龙云资助6万元。据说李济深不但帮梁漱溟弄到从桂林去香港的机票并让其暂住香港家中,还筹集了45000元作为资助民盟办报的经费让梁带去香港(以上均为法币)。但在梁的回忆中,并没有提及资助经费一事。到了香港,中共则通过范长江送来5000(梁说是四五千元)港币(当时港币与法币的汇率约为1:5)。
三
当时梁漱溟在香港办报,中共不但出钱,还出人、出力、出主意,首先就表现在周恩来的建议上。周恩来说:“报纸的言论最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讲话,象毛主席说的以中间偏左的立场出现最好了,站在右边不好,左边也不好,以中间偏左的姿势出现,接近共产党,对共产党有帮助,对全国大局有好处。”这番话对办好《光明报》很有启发和帮助。周恩来还建议到达香港后找廖承志、范长江帮忙,他们是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其次,《光明报》这个刊名,是梁漱溟和范长江一起商议后取的;再次,梁漱溟得到了中共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海外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于是《光明报》得以创刊。
但总的来说,民盟《光明报》的办报立场、经费筹措、人员安排以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简称“宣言”)内容的拟定等大小事情,还是得民盟内部各党派人士具体协商确定。
据梁漱溟说,曾参加筹办《光明报》的青年党的曾琦、国社党的徐傅霖就与梁有龃龉。先是在经费筹措上,徐傅霖与梁漱溟发生争执,坚持由他代表国社党和民盟去新加坡一带向华侨募款就行,民盟就不必再派人;再就是在人员安排上,在报社经济既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曾琦还要往报社里安插闲人,这令梁漱溟非常气愤。
最关键的,还是在“纲领”和“宣言”内容的拟定上的分歧和干扰。此事梁漱溟在《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参见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一文中有详细披露:
民盟的政治纲领早在重庆时即由我执笔写好,并经大家修改同意。但在报纸创刊前一个多月,黄炎培即托人自重庆带来密函并抄件,其中意见是为避免使国民党感到刺激,拟就的12条纲领中有4条暂不发表。……为了消除分歧,能按原定日期(1941年月10月10日)发表民盟政治纲领,经过在港民盟成员多次讨论,和与在重庆的民盟成员多次信函往返,终于决定由我根据原来的12条另起草一个10条纲领。这个改写后的纲领后经重庆方面民盟成员同意,一字不改。而在港的徐梦岩、周鲸文等坚持删去第4条中“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执行”,而在第二条“结束党治”后面,增加“仍委托国民党执政”等字样。结果大家议论纷纭,久久定不下来,最后终于修改为“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建国纲领”……
至于民盟成立宣言的发表方式的分歧,早在宣言起草之前就出现了。青年党曾慕韩首先提出发表时不具名的主张。而后被推为民盟主席的黄炎培又提出要为他个人参加民盟保守秘密;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有人又提议改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而职教社又反对,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为黄炎培是该社负责人,有了职教社的名字,也就等于有了他的名字。于是我又建议以“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名义,或解除我的报社社长职务再发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党曾慕韩以不具名发表的意见未谈妥为借口,拒不起草原应由其执笔的宣言。……最后在万般无奈中,只得服从不具名发表的意见,在《光明报》上刊登了这两个民盟的重要文件。
当然,各党派有不同意见因而产生分歧是很正常的。为避免使国民党感到刺激,“三党两派”领导人不仅建议救国会暂缓加入(最后大家达成默契,救国会暂不参加),还在“纲领”的内容和“宣言”发表的方式上反复磋商,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梁漱溟草拟的政治纲领的具体内容在民盟内部虽有意见分歧,但都不是原则性的、而是具体表述上的分歧。虽说兜兜转转、几经反复,但经历这般曲折、最终发表的《纲领》才是“初步之结合”的各党派共同意志的体现。
不过,各党派有不同意见因而产生分歧也许是令黄炎培担忧而短暂担任主席的原因之一,毕竟成立之初大家就在“纲领”的内容和“宣言”发表的方式上争执不休,今后如何统一各党派意见将是个棘手的大问题。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如赵锡骅的《民盟史话》(群言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所说的:黄炎培担心若以民盟主席的名义署名发表民盟成立的宣言和纲领,以后他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将遇到国民党强加的许多阻碍,遂于出国前提出辞职。
而且,王海波在《民盟历史中的上海记忆》中还指出,黄炎培之所以能够在民盟成立之初就担任主席,旋即又因“赴南洋劝募公债”辞去主席职务,是与他“外圆内方”的处世之道密不可分的。
我们不妨以《黄炎培日记》中记载的相关内容为线索,佐之以梁漱溟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六辑1980年1月),看看个中缘由。
首先,梁漱溟需要辗转两个月,才于5月20日从桂林飞抵香港,而黄炎培却于同日自香港飞抵重庆,与梁漱溟擦身而过。
其次,据日记所载,7月10日得漱溟电:要事待商,盼即来港。得(吴)涵真(笔者注:救国会、职教社成员)港信:去港期为大局宜早,为募债宜九一八后。可知,梁电及吴信催促黄尽快赴港。
再次,接下来这段时间的日记就频繁记录他与左舜生、章伯钧、梁漱溟、罗隆基、张澜、李璜等民盟领导人的联络、磋商,并决定赴港。同时,还不忘与国共首脑通气,真是面面俱到:8月15日,电复延安毛润之等,函恩来转。18日,八时半,见蒋介石委员长,谈二十分钟。19日,上午(凌晨)一时抵香港。可谓姗姗来迟。
8月19、20两日,黄炎培两次与梁漱溟深谈(黄注明“是为第二度”),“黄表示其环境实不容其出名参加同盟”,即黄不愿署名。既不署名,实际上就相当于要辞去主席职务了,黄对于纲领内容、发表时机等问题也就不再固执已见。于是梁马上草成“十大纲领”并写一长信(包括三件请求事项)托人带回重庆。28日,梁约在港民盟同人集议,报告一切,再把相关修改意见反馈回内地,同时准备于9月18日创刊。也就是说,此时黄炎培已有辞职的念头。
据梁漱溟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中披露,9月22日,梁漱溟、曾琦等在港民盟同人在讨论发表民盟宣言及纲领署名问题时,因黄炎培已决定不署名,曾琦于是提出均可以不署名,梁漱溟则坚决反对。梁认为在宣言、纲领上至少要有主席、总书记的名字,并主张改推张君劢为主席。曾不同意。梁就发函回内地汇报。10月3日黄炎培返港。10月5日,黄与梁深谈,梁以此问题告之。黄同意梁的主张,即电渝(重庆总部)请改推君劢主席。而10月8日渝回复说主席非大会不能改选,并维持不署名做法。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其一,早在9月18日黄炎培离港之前(8月20日),梁漱溟就知悉黄不愿署名,有辞职的想法;其二,9月22日的会议后,梁漱溟因署名问题而推选张君劢为主席;其三,10月5日,黄与梁深谈之后,黄同意梁的主张,即电渝(重庆总部)请改推君劢主席;其四,“渝回复说主席非大会不能改选”,说明至少到10月8日为止,民盟总部还没有同意改选张君劢;其五,10月28日中共发表《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首句是“最近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均、张澜先生等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说明可能中共已经知道黄炎培辞职,但恐未知张澜接任主席。
而梁漱溟在《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选编自重庆市政协编《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中说的:“ 9月18日,……其时黄炎培已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此说有误。
另外,此时担任总书记负责民盟总部日常事务的左舜生强烈反对张君劢接任主席,他是想接任主席。青年党在13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占有4席,人数最多。另据说,张君劢的胞弟、交通部长张嘉璈劝其到昆明暂避。经过多方商议,最终由张澜接任主席。有一种说法是,张澜的接任是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的,但更关键因素在于,张澜德高望重、深孚众望,而且无党无派、处事公允,适合调和盟内各党派间的关系,同时他与地方实力派有深广的联系,各方皆认可。
11月16日,民盟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等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及部分参政员参加在重庆举行的茶会,正式宣布民盟成立。
四
可以说,黄炎培的辞职在同盟内部引起了一系列的纷争和变故,并直接影响到政团同盟后来的发展局势。但黄炎培是个做事总考虑万全之策之人,他应该在从菲律宾返港之前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据《黄炎培日记》,黄炎培10月3日抵港后,对媒体提“中国今后所需要的,乃是保育式的民主政治”。5日与梁漱溟深谈,写下“自立,合作”。7日,共曾琦长谈。夜,梁漱溟来,出示所为宣言。当夜作文:《我之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文明志。
10月17日,黄炎培写成《我之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19日,与王艮仲彻夜长谈,“商定今后吾人态度,以社会事业为本位,而注重训练政治人才,提出政治主张,在相当条件下参加政治工作,一切一切求适合政治环境”。也就是说,民盟事务不再是黄炎培工作的重心,但是也会在适当条件下参政议政,提出政治主张。
20日离开香港前,黄炎培精心安排在胜华酒店招作家开茶话会,到者陈翰笙、恽逸群、金仲华、柳亚子、陈乐素、沈雁冰(茅盾)、千家驹、邹韬奋、沈志远、胡仲持、周鲸文、羊枣(杨潮)、夏衍、乔木、范长江、萨空了等。黄将当日出版的表明其心迹的《我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分赠在座诸位,“谈甚欢洽”,目的达到。
当天深夜飞离香港,到重庆后,马不停蹄地与沈均儒、左舜生、章伯钧、张君劢长谈。接着又与周恩来长谈。在对盟内外各党派领导人交心表态之后,对所作的《我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继续补充完善,以扩大影响。并言,“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对国民党方面,他同样应对自如。他11月8日得杜月笙信,附有《光明报》剪报。9日晚上,他写信回复杜月笙,叙述午间见蒋公情形(蒋并没有问起民盟成立之事),以及此间对同盟情形。最后表态,“梁文无误,吾生态度倔强到底”。表明了鲜明的立场。
应该说,经过黄炎培如此这般奔走沟通、多方周旋,辞职风波总算尘埃落定。为宣布民盟成立一事,从11月10日到14日,在张澜主席的主持下,民盟领导人多次邀请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在特园或左舜生家会谈。民盟常委除梁漱溟在香港外,悉数参加。
值得注意的是,据《黄炎培日记》12月1日载:“9时,特园盟会,到者表方(主席)、君劢、舜生、幼椿(李璜)、可玑、御秋、伯钧、努生(罗隆基)、赓陶、张若谷(湖大)、杜斌丞(虎参)、张云川、张文(潮参)、彭泽民。(常)表、载、君、舜、幼、漱、慕、钧。(执)加努、可、映(映芙,即丘哲)、赓、御、鲸、乃光。”从中可以窥探一二:其一,参加会议的杜斌丞(救国会,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和张文(李济深的高级参议)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已经入盟;其二,讨论的新常委有张澜、载(笔误?应代表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梁漱溟、曾琦、章伯钧,说明除了之前的五大常委及张澜主席,将增加两位青年党领袖李璜和曾琦。若如此,则青年党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提高;其三,讨论的执委加罗隆基、林可玑、丘哲、杨赓陶、冷御秋、周鲸文、乃光。疑问有二:一是罗隆基、林可玑、丘哲、杨赓陶、冷御秋之前已经是执委,拟增加的应该是周鲸文、乃光。二是乃光是否是指国民党左派人士甘乃光,存疑。
但无论如何,这次会议的人事议题并没有立即得到落实。直到1944年9月,在民盟全国代表会议上才选举出新的领导成员。
另外,由于之前救国会领导人多次参加民盟组织的各种会议,并与民盟一致行动。到了1942年1月,在张澜的主持和引导下,经多数人同意,民盟中央讨论决定,邀请沈钧儒及救国会全体加入民盟。自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真正成为“三党三派”的联合组织。
民盟成立初期,盟务工作一直由担任总书记同时又担任青年党秘书长的左舜生来负责。青年党早在1938年就在国统区取得合法地位,加上当时民盟总部活动中心在四川重庆,四川又是青年党的基地,这导致民盟的许多盟务工作都由青年党出面代办。这种内、外环境都有利于青年党把持盟务。(参见韩忠金、孙信《中国民主党派简史》,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受战争、地域等因素影响,号称“川北圣人”的张澜有“表老不出川”之名声,在四川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李璜、曾琦都是四川人,因此民盟总部一开始把组织发展的重心放在四川,如张澜、李璜等就在成都发展了一大批盟员。
到了1942年,救国会参加了民盟,此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章伯均和负责宣传工作的罗隆基开始把目光投向四川之外。而救国会、第三党在中共的支持下,也考虑到外地建立民盟地方组织。
1942年9月,李伯球(第三党)带着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民盟总部章伯均交代的使命,回到桂林后立即与梁漱溟会面,转交民盟总部请梁漱溟出面主持广西盟务的信件,并协商成立民盟地方组织相关事宜。他们邀请同是民盟成员的罗子为(乡建派)、周鲸文、张文、曾伟(第三党),以秘密的形式,成立了以梁漱溟为首的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不久,救国会成员陈此生、狄超白(中共)、张锡昌(中共)、千家驹、胡仲持、金仲华也陆续加入。
李伯球在相关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就离开桂林返回广东。他抵达韶关后,与李章达(救国会,国民党左派)协商建立民盟地方组织。经过一番筹备,很快就成立了以李章达为首,以李伯球、杨逸棠、郭翘然、胡一声为成员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
1942年年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委员会派罗隆基到昆明筹建地方组织。1943年,中共南方局派以救国会成员身份加入民盟的中共党员周新民到昆明开展工作。5月,罗隆基、周新民、潘光旦(国社党)、潘大逵(救国会)、唐筱冥(青年党)、李公朴(救国会)等6人,便建立了以罗隆基为主委的民盟的第一个地方支部——昆明支部。当然,与民盟桂林核心小组、韶关核心小组一样,民盟昆明支部与中共及救国会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先后加入的云南大学潘大逵、楚图南、冯素陶、费孝通,西南联合大学潘光旦、闻一多、吴晗、曾昭抡等都是著名的进步教授。
但另一方面,直到1946年,民盟领导人在公开场合都不承认中共党员加入了民盟——“直到今天为止,民盟之内没有共产党员参加,有少数的国民党员,百分之八十的盟员是无党派的。”(参见李公朴《民盟的历史与组织》,载《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七期)“根据与共产党所成立的一个君子协定,任何人均不能是同盟盟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参见曾昭抡《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主张、理想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载《民主报》1946年10月19日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是以罗隆基(已是无党派身份)为首的云南省支部提出来的。众所周知,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主要成员均有党派所属,仅有个别没有党派关系者。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广西桂林、广东韶关以及云南昆明等地相继建立地方组织,而新吸收的盟员中有些是以无党派身份加入的。尤其是1944年的民盟云南省支部,“无党派的盟员对有党派的盟员,已超过二十对一的比例”。这样,民主政团同盟再以三党三派号之,就名实不符了。当然,云南省支部如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想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这除了形势发展需要外,也带有对青年党把持盟务工作不满的因素。当时,左舜生作为总书记,虽然总负责民盟总部的日常事务,但负责组织工作的章伯钧和负责宣传工作的罗隆基也能够并且应该参与其中。不过,由于张澜住在成都,平日与在重庆的总部沟通不多,因此左舜生利用这一点包揽了民盟的日常事务,这就引起罗隆基等人的不满。
更重要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处于国共之间的民主政团同盟,在加强内部团结的同时,也需要对外发展。如果继续将组织局限在党派关系之内,无疑将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拒之门外,这显然不利于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正是考虑到这一现状,云南省支部经过多次磋商,正式向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建议“把原来的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把‘政团’两字取消”。罗隆基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肯定民盟不是以‘政团’为单位的联合体,而是政治主张相同的个人的大联合”。民盟中央接受了云南省支部的建议,于是,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改变组织名称,决定取消会员制,以后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以利于吸收更多的人士。(参见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主同盟》,2009年12月23日在民盟中央的报告)
最后,我们不揣浅陋,对民盟改组之前(政团同盟时期)内部各派别的情况作一番粗浅的小结:
第一,民主政团同盟是以“政团”为单位的联合体,主要是由“三党三派”组成。但是“三党三派”之中,党和派还是有区别的。
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都是抗战前就存在的政党,它们在国民参政会上,均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实体遴选出相应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就说明国民党事实上已经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尤其是青年党,俨然有盟内第一大党的趋势。而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是作为文化团体提出遴选人选的,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充其量只能算政治团体而已,因此在形成本团体的政治纲领、组织系统、纪律机制等方面,与“三党”不可同日而语。而“三派”之中,职教社因黄炎培的存在,自然有其相对超脱的地位;由于救国会入盟较晚,在初期话语空间有限;倒是乡建派最没有存在感,原因在于,与其说梁漱溟是乡建派领袖,不如说是民盟创始人。因为他认为盟内应无小团体利益,各党派应齐心协力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
第二,政团同盟除了“三党三派”以外,还有其他派系或者团体的成员,也以无党派人士或其他身份参加了成立之初的民盟。
其他派系或者团体的成员,不仅有民主宪政党的领导人伍宪子,东北同乡会的周鲸文,以及桂系的甘介侯,还有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参加民盟的杜斌丞(救国会,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和张文(李济深的高级参议)。此外,还应加上昆明支部的“教授派”和以救国会成员或其他身份加入的秘密中共党员代表的派别。
第三,黄炎培的辞职在同盟内部虽引起了一系列的纷争和变故,但黄炎培在这一过程中长袖善舞、比较妥善地处理了这一风波。
黄炎培作为民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始终参与民盟的活动,对民盟的成立和发展是尽了心力的。他人脉特广,而且社会事务繁多。抗战中,黄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也不是偶然的。黄炎培既有不肯当官的美名,又有不愿敛财的声誉。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他出于个人处境原因提出辞职,决定今后“以社会事业为本位,在相当条件下参加政治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张澜接任主席,事实证明是最合适的人选。“端方持重、老成谋国”的张澜提升了民盟的声望并领导其走向正确的道路。
政团同盟之所以不能算为一个政党,首先是因为盟内各党派人员并不会而且也不需脱离他们原来所属的政党;其次就因为它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政纲。但是这并不妨碍民盟的团结,因为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无疑是全体盟员的共同主张,这可保证他们能够一起为民主运动而奋斗。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澜深知这一点。正是他在斗争实践中高擎民主、团结、抗日的大旗,“没有党派成见,只有政治主张”,并以个人的影响力和威望团结“三党三派”,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后,为成为当时除国共两党以外的的第三大党奠定了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民主同盟史》,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
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
3、《云南民盟史》,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编,北京:群言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
4、黄炎培《黄炎培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
5、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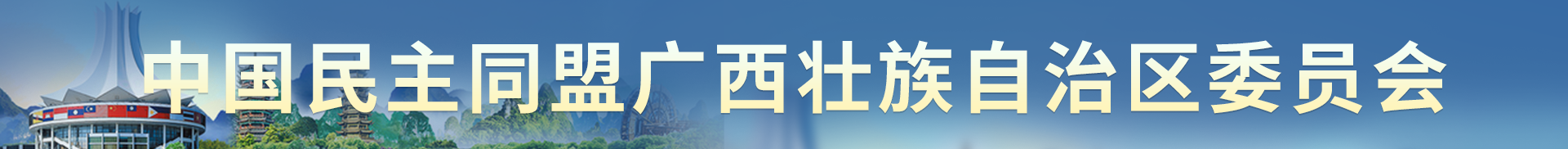

 桂ICP备08100227号-1
桂ICP备08100227号-1